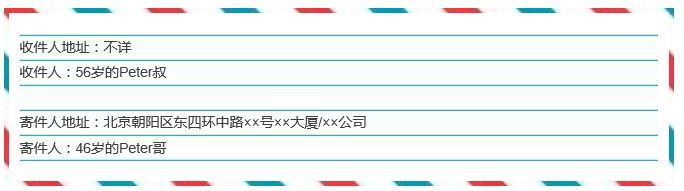
Peter:
你好(其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看信时的你是否真的过得好,但是出于书信格式的要求在此不得不和你客套一下,权当你一切都好吧)。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因此现在的我感觉怪怪的,一方面觉得有很多话想讲,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甚至还有点不好意思。虽然在过往的四十几年中我给父母、家人、朋友、恋人、同事写给无数封信,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产生自己给自己写信的冲动—直到一个月前参加完上海的前公司老友聚会。既然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特殊的信,那就让我先说说这次聚会吧,或许聊着聊着我就能找到思路从而最终将这封信完整的写完呢?

▲懂我的真爱粉们肯定知道这是聚会必不可少的
D公司是我的职业生涯里呆的时间最久的一家(11年),所以在那里有不少老友故交,每隔一段时间大伙总会找个由头聚一聚,比如说前阵子就是为了欢迎一个HK的老朋友来沪,因此我专程从北京飞过去和他们相聚共度周末。
按照惯例当地的朋友们组织了全套的节目:吃饭;喝酒;打麻将;唱歌……这次一共来了5、6个人,其中就包括一位比我整整大十岁的“老同事”(其实该如何称呼他令我颇费了一番脑筋:在D公司里我和他前后共事了快10年,因工作的关系双方交集非常多—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基本上停留在“同事”这个层面上,直到他从公司离职之后大伙才走的近了许多),当时他已经从公司“被”退休快半年了—这些年IT行业总体都不行了,裁员潮一波连着一波,而像这位老同事般的人就是裁员最好的目标:年纪不轻了(55-60岁);薪水太高了;发展潜力不大了,你说不裁这些人裁谁呢?
当然公司一定会赔偿一笔“分手费”再加上他自己过往的财务积累生活应该不会成问题,但是对这些忙惯了的人来说无事可做实在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昨天还是管理着横跨全球或者某一个大洲;拿出差坐飞机当打的;手下簇拥着几千人的团队;每天以听别人汇报和给别人做报告为生的高管,一夜之间被打发回家啥也不是了,你说让他怎么能适应呢?

考虑到身体和心理状态还完全可以继续工作,因此刚退下来时他也曾经蛮积极的找过工作,但是很快就不了了之了:倒不是说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惯了大公司的高管,放不下架子也不愿意主动调整自己对工作的期望值,结果就只能是高不成低不就,到最后自己的心也慢慢地冷了下来,开始不得不接受现实了—这就是我们聚会时这位老大哥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明亮的公司会议室日光灯下,我和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开过无数次的会—那时的他咄咄逼人意气风发出了名的难搞;在觥筹交错的酒桌上,我和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吃过无数次的“政治饭、业务饭”—那时的他长袖善舞神采奕奕一幅不做酒桌中心誓不罢休的架势;但在灯光柔和香衣云鬓的KTV里,我和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好像还真没有交集过—抱着窥探别人隐私的“猥琐”心理,我本来很想看看除了那副在我心中早已熟悉的“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积极向上”的样子以外,这家伙还有什么不为我所知的另一面:更火爆?更龌龊?还是将道貌岸然进行到底的嘴脸?
可是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几首英文的老歌唱罢,这位老朋友就将自己的身体陷入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漠然地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眼神里充满了难以掩饰的落寞,整个人也渐渐变得迷离,最后彻底游离于空中失去了声息,全然没有了我心目中熟悉的那个样子。我一时也想不到该用个什么合适的词去形容他,直到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悄悄的趴到我的耳边说: “Peter,我没想到才短短的半年,这位老兄就变得这么颓。” YES!就是这个词:“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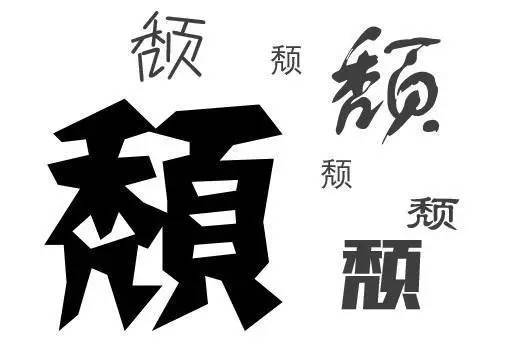
那晚从KTV出来大伙一起在清冷的街头打的,因为这个老同事的家就在上海而且离的不远,因此他和大伙告别后就先行离开了。望着他独自远去的背影,我点着了一根烟深深的吸了一口,合着已然冰冷沁脾的初冬夜风,将这口烟狠狠的吐向了空中,然后在心里默默的对自己说:
操!老子将来绝对不要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上海回来后关于“职业生涯终点”的思索还没有整利索,紧接着就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把我的情绪搞得更低落了:因为踢球的缘故,我的右膝盖整个肿了起来,快一个星期了还无法消肿,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才发现是因为右膝半月板磨损严重引起的:30岁时我还能坚持每周踢一场球,可现在一个月能踢一次就不错了,而且踢完了后浑身酸疼四肢无力前后没有一个星期根本恢复不过来。那天按医生的要求拍了膝盖的X光片,拿到片子后大夫一边看一边坏笑着对我说:“张先生,改打高尔夫或者老年门球吧,踢球已经不是您这个年龄适合的运动了。” “可是我只爱踢足球啊,玩其他的运动实在让我提不起精神。”我心有不甘的说道。“但是你的半月板不答应啊,是时候找找其他的替代品了,因为你别指望能有一项运动是可以让你享受一生的。”

▲我如此迷恋足球,膝盖里的半月板却不解风情
我从十几岁时就开始迷上了足球:小时候迷是因为踢球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大人,而且很帅可以吸引女生注意;再大一点了开始懂得欣赏这项运动的美以及从中感受到的快乐—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一个个踢球的黄昏,和一堆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在操场上出一身臭汗,互相骂着粗话推搡着冲撞着为了一个球进没进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每次都要踢到太阳落山才不情愿的收脚,一堆人挤在操场边的水龙头下痛快地冲个凉再喝上一肚子冰凉的自来水,然后懒散的坐在街边的马路牙子上,就着昏黄的路灯光,7/8个人一边分享着同一根香烟一边聊着隔壁班的漂亮女生,在大脑里幻想着美好但又有些模糊的未来……与其说我现在迷恋的是足球,不如说我在心里放不下的是它曾经带给我的那些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那些流过的汗/抽过的烟/付出的友情和爱过的人,我知道它们都已经离我而去而且永无再现的可能,但是越是如此那种迷恋就愈加浓烈浸入骨髓无法割舍……可遗憾的是:膝盖里的半月板这时却不解风情的提醒我:是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因为足球绝对不是能够伴随终生的运动,与其执着于过去不如想想未来吧,想想什么是可以让你在接下来的10、20、30年中还能依赖和享受的运动—比如说老年门球?

足球如此,职业生涯不也同理吗?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无需回想,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幕幕令人激动的职场辉煌瞬间至今清晰可见:比如说23年前,那张贴在狭窄的麦当劳员工休息室里的海报—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张晋升通知:从10多个同期的管理培训生中第一个被提升为第二副理+50RMB/月的调薪!比如说17年前,可口可乐的HR发给我的那封录取通知书,让我将“作为第一个通过外聘直接担任部门主管”的自豪挂在嘴边吹嘘了大半年;比如说在五年之内连升三级同时管辖的业务范围从大陆到大中华区再到北亚然后亚太最后管理一个全球运营业务……
我一直以为这就将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和终点,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最初,你是我的最终,你是我的唯一。”但遗憾的是,六年前的一个“偶然”之举,让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在职业生涯之外又看到了一片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令人痴迷也让人神伤:先是在企业做内训,做着做着就跑到了厦大MBA,进而川大/河海大学MBA中心担任企业导师;然后开始正式挂牌讲课(公开课/内训课/专题讲座/意见分享/微信课/音频课/视频课……);最后居然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写上了文章还胆敢传播思想,结果招惹上了大麻烦并最终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详情请参见我的公众号,或者用我的名字在知乎/新浪/领英/虎嗅/喜马拉雅上搜索相关的文章和故事梗概,唉,提起来都是泪啊)。

▲为满足各位八卦的心,把APP图标都给找好了。
现在回头看看这一切其实都是宿命—虽然发生时貌似是一个个独立的偶然(拼职场/想教书/迷写字/惹麻烦),但如果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世间的万物其实早早就已经被上天安排的好好的了,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如此一想我就对46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释然了:比如说18岁时为啥死活都不想考离家近的大学,恨不得跑到天边去;比如说19岁时只身一人跑到那个大广场上和十几万人睡了半个月差点没死在五月35号(郑重申明一下:绝对不是群P啊!你们别想歪了,其实大家各睡各的而且连衣服都没脱啊);比如说明明活得好好的可人到中年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于是就哭着闹着要重新来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辛苦半辈子赚到的一切财富;再比如说当发现一直以来自己深以为傲的所谓的“职业成就感”原来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而让自己内心真正激动、执着的是写字,分享,教书时,那种“去”还是“留”的抉择让我内心痛苦的夜不能寐辗转难眠……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什么应该是我人生的下半场?什么是自己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最想做的事?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做这件事,那到死的那一天自己会不会满地打滚死不瞑目呢?绞尽脑汁的思考过后发现答案无非有两个:
一、是继续职业生涯努力再向上爬,赚更多的钱/负责更大的区域/担任更高的职位……直到被干掉而又无力改变的那一天?理智和24年的职业经历告诉我应该选择方案一(情怀是不能当饭吃的),而且这也是身边像我这样40岁左右/已爬到一定位置/拥有还算丰厚收入的心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们大多选择的道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被那个让我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在职业生涯之外开启的另一扇窗里的风景反复的撩拨,让我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如今的工作和职业对我来说渐渐变成了一种“维持”—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走吧—放弃不下几十年奋斗换来的这份回报(钱/社会地位/稳定的环境);留吧—其实内心早已对眼前的这份工作失去了当初的热情,支撑着自己的与其说是对职业成就感的追逐,不如说是发自契约精神的责任感和20多年来早已养成的惯性(没错,就是这个词—“惯性”),再加上对未知领域的恐惧和迷茫(我现在一想到下个月开始没人给我发工资了,就要立刻提着裤子往茅房跑: 不是因为老男人常有的肾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也就是俗话所说“吓尿了”)。
二、还是勇敢的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想改变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做出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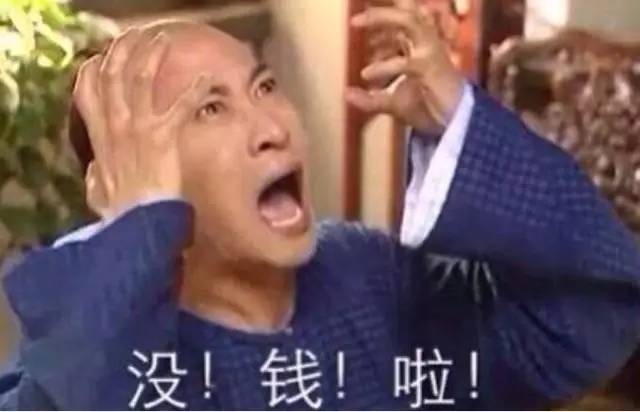
个性使然吧,像我这种骨子里清高叛逆以拥有“不随波逐流坚守个人独立思考能力”为傲的人,是无法容忍自己接受“因为隔壁老王就是这样活着的,因此我也要这样活着”这种犬儒思想的,这也就是为何在过往的几年时间里,我是如此煞费苦心的在职业与情怀之间如走钢丝一般的努力做着平衡—曾经有那么一度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鱼与熊掌兼得,接下来只要再多给我点时间;让我再多做一些准备(多赚点工资好让财务的准备更充分一些);多结识些人脉(好让未来的教书/分享/做研究更有市场);最好再考几个资格认证(让今后的收费档次更高一些)……然后等到那个完美的临界点出现,我就可以华丽变身从此不再去做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痛痛快快的做一次自己! 可惜最终残酷的现实好好的教育了我,这一切不过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如果你不去勇敢的改变,或者被改变……
那就这样吧:
看来人生中好像真的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回事儿的,就如同“如果我将来财务自由了, 我就要*&^%$#@%……” 一样,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
那就收手吧:
如果人生的上半场应该更多的关注加法(钱/地盘/职位/名利),那现在到了该做减法的时候了,免得让自己成天挣扎于想说又不敢说透/说痛快/说过瘾,想做又不敢做到最好/玩到极致—因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职场禁忌。这就像在屠呦呦获奖之前,每次和老外解释“中国有几个诺贝尔获奖者?”时我都只能尴尬的回答:“一共两个:第一个莫要说(莫言),第二个不能说。”
那就认命吧:
既然不想憋屈的做锦衣玉食/位居高位的华丽笼子里的哑巴,那咱就安心的穿上布衣粗履,从此耕田教书,做一个想唱就唱心胸坦荡的直肠野夫,不也快哉!
那些意料之外发生的事,我记得小时候写信,老师通常都会让我们在结尾处喊上几句口号,或者抄一段名人名言来提升一下整封信的B格。有鉴于斯,在此我也特别摘抄了一段读者在我文章下面的留言作为全信的尾声,希望它可以成为我今后独自走夜路时手中的一根打狗棍,孤单害怕的时候在空中挥舞两下,权当给自己壮壮胆儿打打气儿:
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拉拉杂杂的讲了一大堆也不知道你都听明白了没有—56岁的Peter叔?希望十年后的你读到这封信时没有为自己今天的决定而后悔。最后也祝46岁的Peter哥,一路珍重……
顺颂冬安
2016年11月21日万籁俱寂
文/张思宏
来源:没空读书







 /3
/3 
